一个男性被诬陷偷拍后,自证清白的200天
2023年8月,“成都地铁偷拍事件”一审立案,我是从那时起关注到这个案子的。事件发端于2023年6月,30岁的小何在成都乘坐地铁,突然被两名年轻女孩高声指认鞋面装摄像头偷拍。赶来的警方调查后给他澄清白,分析是光线导致的误会。
这起普通的社会新闻,混在信息洪流里显得再普通不过。但事情远不止于此,这之后,小何主动在微博曝光自己被诬陷偷拍,文章中他写道,“女孩们没有道歉的态度,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” 他遭到了莫大的羞辱。这条长微博被阅读超过4000万次,登上了热搜。
巧合的是,就在小何被误指偷拍的前几天,另一起发生在广州地铁的“张薇事件”——年轻的大学生女孩诬陷一名农民工“偷拍”。两起社会新闻同时演变成了网络事件,一场大众的审视开始了。一些网友质疑小何所说的真实性,要求他拿出证据,也有人说“肯定是因为你长得猥琐别人才会怀疑你。”
受舆论影响,也害怕被网暴,小何决定借助法律手段,撕掉“偷拍者”的便签,寻求对方一个公开的道歉。半年的时间里,他先后经历了报案未立案、寻找证人、一审立案、败诉,二审上诉的过程,至今事件仍未结束。单看起因,这无疑是一件小事,一个困惑我的问题是,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实现了为自己正名的目的,为什么还要坚持?
2024年春节前夕,我与小何在成都见面。交谈中,小何反复提到两位女孩的淡漠和轻飘态度,以及毫无意识地道歉,都让他感受到愤怒和一种强烈不对等感。一审结束后,网络上出现新一波评论,他又一次陷入自证清白的漩涡中去,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,“舆论,身边的朋友都在等待反转,当他们说了很多之后,我自己都相信了,就好像我鞋子上真的有摄像头。”
热搜之外,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在“女性面临偷拍”的情境下,举报者和被诬陷者都处在各自的困境当中,恐惧感被无限扩大化,当我们本能地不相信别人而造成互相伤害和误解时,也是社会信任崩塌的开始。
指控
2023年12月,一审宣判,小何没能等来公开道歉。过度维权成了他新的标签,带来又一轮网暴。网络上,有人用“何五万”调侃他,源自诉讼中他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5万元,这一诉求法院也不予支持。
“你说这公平么?我投入了巨大的成本自证清白,那两个女孩对我的付出似乎毫无感知。”谈起此事,小何提高了声调,语气中包含一种愤怒,一种失望。
持续半年打官司,他状态不好,影响到了工作,2024年春节前夕,他向单位提出辞职。“没有这件事不会辞职,官司打赢了也不会辞职”,他说。
小何个头不高,面部白净,随身背着双肩包,说一口川味普通话。他已经工作8年,先是在宁波做工程造价,两年后定居成都,买了房,每月背负房贷5千元。上一份工作他是部门的主管,工作之外,他喜欢踢球,偶尔周末也会和朋友去爬山。
他看上去并不起眼,就像这座城市中的其他普通上班族一样。直到“偷拍者”的指控突然被推到他面前。
他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场无妄之灾,面对媒体的镜头,他已经讲了很多遍了。2023年6月11日晚上,他和同学聚完餐,从成都地铁6号线犀浦站出发,坐地铁回家。途中,他给一对老夫妇妇让了座,站到了车厢中间扶手柱的位置。
列车行驶到火车南站,距离他大约两三米的座位上,两名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,大声喊:“你是不是在偷拍,我怀疑你在用小型摄像头偷拍。”
当全车厢的目光都聚焦到自己身上时,小何才意识到,自己正是被喊话的那个人,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瞬间蒙了。
很快,地铁安保人员闻声赶来,“夹住”了他的手臂,询问女孩是怎么回事。“我看到他鞋子在闪烁绿光,上面装有摄像头,在偷拍。”女孩愤怒地说。另一位女孩也补充道:“就在他鞋带最前端,刚刚闪了绿光,我们看到了,他就关了。”
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,小何回忆那一刻的感受,“就像在众目睽睽下被逮捕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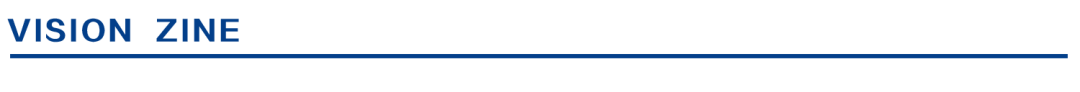
互联网的“魔性”一度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,“舆论,身边的朋友都在等待反转,当他们说了很多之后,我自己都相信了,就好像我鞋子上真的有摄像头。”
让他感受到刺痛的是来自熟人的质疑,一位朋友调侃他,“为什么不说我偷拍要说你偷拍?”讨论得多了,小何也认为这件事是不光彩的,“就像一个污点”。
赶在春节前夕,他向法院提交了二审申诉。我问他,虽然一审败诉,但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为自己正名的目的,为什么还要继续?他表现出不满,“为什么你会觉得已经结束了?调解就算结束了?我做不到,发上网也不算结束,一审判决的结果我也无法接受。”他承认自己被互联网的舆论所裹挟,热度越高,压力越大,越需要一个好的结果。
让两位女孩公开道歉是他的最终诉求,“怎么才算是公开?”我问,他说:“可以是一个公开的道歉信,或者视频。”并补充道:“我要保护她们的隐私,脸打上马赛克,名字化名一下。”
可是他又表示不满意,“道歉还要化名,你懂那种感觉,双方还是不对等的。”
被诬陷的冤枉与被偷拍的恐惧
在被指控“偷拍者”之前,小何从未关注和听说过“女性偷拍或性骚扰”事件。一些媒体记者向他抛出一个问题,你如何看待女性频繁被偷拍。一开始他不愿回答,有意遮蔽,当避无可避时,他逐渐看到了大量的相关情况。
现实中女性面临“偷拍”广泛存在,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2023年英国广播公司(BBC)国际频道调查小组“BBC之眼”发布了一条名为《追查“痴汉”——谁在售卖中国日本性侵偷拍影片》的纪录片,揭露了一个位于日本东京的售卖偷拍性侵视频团伙,一些视频就拍摄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车厢。它们被传播,被明码标价,被观看。
在和小何见面之前,我试图在网上寻找有过被偷拍经历的女性。24岁的“番茄”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。2023年8月,她和男友在厦门一家购物广场一楼逛街,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,他环抱手臂,同时一只手将手机支在胸前,像是在拍什么东西。
“番茄”感受到一丝异样,她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在拍自己,快速地走了过去。之后,她迅速回头,想要确认一下,她看到了一个场面,那个男人用反拿手机的方式,拍摄自己。她大声指责,男子才放下手机,快速离去。
被偷拍的这一幕没有被身边的男友看到,当“番茄”与他说起时,她的男朋友第一反应是反问:怎么知道他是在拍你。他不相信她被偷拍。当女友提出保护的请求时,他感到为难,“我不能去看对方手机里的相册,很没有礼貌”。
“番茄”认为按照那个男人的拍摄角度她肯定是入镜了,侵犯到她的肖像权了,想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陌生男子的手机里,她感到害怕不知道照片会流向何处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,她和男友商量,让男友也拍偷拍者,互拍,这样既可以提醒偷拍者,也可以留下偷拍的罪证。
另一位小A也遭遇到了类似的经历。那天,她去成都东站坐动车,她穿了一件新裙子,也化了妆,原以为这是正常的装扮,但还是被偷拍了。“我在犹豫对方是不是拍我,我都看向他了,对方还是举着手机”,小A说。她不敢上前要求对方删除照片,事后又感到后悔。
她们谈到面对偷拍时,第一反应不是愤怒,而是怀疑,“他真的是在拍我么?”,第二反应是害怕,继而愤怒。但她们往往没有更好的办法,小A和友人聊起这件事,女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,“大家都认为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,拍就拍吧”。
“你能明白女性的处境么?” 我向小何细数女性的困境时,再一次问他。“我觉得你们说得很有道理,能理解,但是我很难共情。” 他回答,语气真挚。
他认为女性被偷拍是少数的个例,他始终感到困惑,“偷拍的尺度在哪?在公共场合拍风景,拍到了路人,也算是偷拍么?”相比之下,他觉得一些人在借此炒作,为了流量,博人眼球,随意给人贴“偷拍者”,“猥琐男”的标签,没有任何证据,“你不觉得可怕么?男生的名誉也很重要。”他强调。
网络上,小何的社交账号几乎成了“被冤枉偷拍”的代名词,曾有5名网友自称与他经历相似,想一起维权。“现在他们全都放弃了。”维权太困难了。
他提到最近的一个例子,公交车上一名女士指认一名男生偷拍,并拍下了照片,发到社交账号上。帖子被男子的一个朋友看到,得知后,男子报警,警察让女子删帖。男子说自己是被诬陷的,他想要起诉该女子。他私信小何,想请他出出主意。“如果这个男生把这口气咽下去,你觉得公平吗?我觉得不公平。”小何说。
在他维权的过程中,有网友质疑“为什么要跟两个小女孩计较”,他始终认为,事件中,“诬告者”与“被诬告者”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对等,他有“坠入深渊”的风险,而“诬告者”却不用付出什么成本。他坚定地选择用正当方式维权,“要是我当时动手了,在后面的处理中就会非常被动,身着长衫,这样的代价对于我来说还是大了点。”
他又接着补充,“如果是正常怀疑,我也能接受,怎么不能接受呢?但我没有做,你就应该道歉。”
“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”小何的代理律师刘丹说,他认可两位女士的行为,她们有权利合理怀疑,但同样自由也有边界,“这个边界就是法律的边界。”
交谈的最后,小何提到余华的短篇小说,《黄昏里的男孩》,小说里的小男孩因偷吃了一个苹果,被人掰断了手指。
这则寓言让他联系想到了自己。“恶也会传播。如果我没有得到正义,下次遇到这种情况,我就动手了。”
